《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》第二十九篇
為中國史學的實證化而努力
我研究北方民族只有十年功夫,之於畢生從事某一課題的專家來說,
批評意見主要是關於我的方法,
一位語言學者建議我常備一本高本漢(Bernhard Karlgren)的《漢文典》(Grammata Serica Recensa),他說:「
事實上,這不是什麼「科學規範」而是一種「文化意識」,
上一世紀,由於比較語言學方法的應用,「漢藏語系」
推行實證的手段,之於中國學術非常重要。譬如,匈奴首領的稱號「
《詩》俾爾單厚;
《禮》歲既單矣,世婦卒囂;
《書》乃單文祖德;
《左》單斃其死;
《禮》鬼神之祭單席;
《詩》其軍三單;
《書》明清於單辭。
其實,這些「單」出處都是它的「字源」而非「音源」,
對於「單」的讀音可有兩個非漢語的證據。其一,《漢書•匈奴傳》
西人高本漢和國人王力的工作是重要的,乃至偉大的,
甲骨之「帚」字是「婦」,早已被郭沫若破解;但甲骨氏族名「
司馬遷還遇到過更古老的語言或文字,他在〈五帝本紀〉結尾時說:
大史公曰:學者多稱五帝,尚(上古)矣。然《尚書》獨載堯以來。
我以為「雅言」或「雅馴」是指後來形成的漢語,
上世紀甲骨文字的成功解讀,中國史學的實證化有了長足的進步。
顧頡剛是二十世紀有大膽思想的先進人物,
《後漢書•西羌傳》又說「渭首有狄、豲、邽、冀之戎」,為什麼「
顧頡剛以「疑古」成名,其實那並非真是「疑史」,大多只是「
科學是知識的進化系統,即基於一些認識背景和方法,
語言學是人類學的當家學問,
2008年一月六日
202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訂
|
|
黄春光: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。。。。。。
|
李冰天、邱路光、林豆豆、陶斯亮、罗东进、黄春光在《李作鹏、
李冰天:父亲李作鹏临终前说自己的骨头都是红的
尊敬的各位老大哥、老大姐,尊敬的各位战友、朋友、同学们,
大家好!
今年四月是我父亲和邱会作伯伯诞辰一百周年。
我父亲和邱伯伯都是江西老表,是穷苦人出身。
在“红旗卷起农奴戟,黑手高悬霸主鞭”,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
在我父亲的遗物中,有他精心保存了—
2011年,我父亲的《回忆录》出版之后,我和我弟弟李炎天,
今天,我们将纪念册和画传献给我们敬爱地父亲和母亲。
《沧海永生》和《邱会作画传》都收录了两百余张历史照片。
在这些老照片中,同时还记录着父辈生前各个时期与几百位老领导、
这些历史照片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回忆,
回顾戎马四十年,邱伯伯说:“我们家是三代同堂闹革命,
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是革命军人。面对生生死死和起起伏伏,
晚年,邱伯伯对胡阿姨说:“我是江西的穷苦人,
在我父亲病重的最后时刻,他把我叫到病床前。他右手指着左臂,
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遗言。
现在,每当我翻看这些照片时,仿佛当年的战火硝烟还未散尽,“
苍茫大海,波涛滚滚。那里将是我父亲、母亲永远的归宿,
此时此刻,我们在这里追思先辈,缅怀英烈,牢记革命传统。
谢谢大家!(李冰天系李作鹏之子)
邱路光:父亲邱会作说自己后半生吃了“共产党”的苦
我们这个会是很真情、很友情、很亲情的聚会,请老大哥、
我父亲生前常说:你看天上的星星这么多,中国革命是群星灿烂的,
父亲说他的历史很简单,参加革命穿军装,被打倒脱军装;
父亲一直很怀念我们革命队伍的领袖,怀念自己的老领导、老首长、
林豆豆:对革命的历史遗产应当有更深刻的思考
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会,向大哥大姐及弟弟妹妹问好,
我想以此次勉励大家。谢谢。(林豆豆系林彪之女)
陶斯亮:我们红色的后代应当支持习近平改革反腐
没想到让我讲话,我本来昨天晚上想去买一束白色的花束,
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?因为我接到春光给我发的邀请通知后,
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这源于一段历史吧。我这个人啊,
可是呢,人对自己的一生所作所为都是要负责任的,
我觉得现在今天参加这个邱会作叔叔和李作鹏叔叔的这个活动,
所以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,我觉得不论是林彪叔叔,永胜叔叔,
我觉得我们父辈用革命的一生,
我们现在被人叫什么高干子弟、什么官二代、什么太子党,
还有就是我们也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的改革,
我觉得我们红色的后代,我希望我们发挥我们的正能量,
谢谢。(陶斯亮系陶铸之女)
罗东进: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都很厚重
今天参加李作鹏叔叔、邱会作叔叔百周年我感慨而说。
黄春光:天下是父辈打下来的我们不能背叛他们
今天看到这么多朋友、这么多老同学,
和邱会作叔叔那感情就会更深一些,为什么呢,
我从小在北京上学的时候,就是回到邱会作叔叔家中过周日,
还有就是在延安时期,我父亲44年初刚到延安不久,
所以说,我父亲他们一代的战斗友谊是很深很深地,
作为他们子女,我今天也要向大哥大姐们弟弟妹妹们表个态:
我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,非常感慨地说,我们这个党是多灾多难的,
亮亮姐曾经说过一次话,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,
谢谢大家!(黄春光系黄永胜之子)
本文文字来源第四野战军第一门户网站,共识网综合整理,
|
朱学渊:为《东北拉响人口警报》欢欣鼓舞
复活节岛的人口红利(维基原文,朱学渊删节改题) |
• 复活节岛
西班牙语:Isla de Pascua,或根据当地的语言称拉帕努伊岛(Rapa Nui),另有依照英语音译为伊斯特岛(Easter Island,朱学渊按即复活节),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,
|
图片1、复活节岛地图
|
1722年的一个星期日,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探险家雅可布•
|
图片2、复活节岛位置
|
• 原住民的由来
由于没有文字资料的记载,复活节岛最初的历史已经无法重建。
|
|
图片3、 勤劳勇敢的岛民祖先
无法确知波利尼西亚人何时抵达该岛,
挪威的著名人类学家托尔•
• 文明的初始
今日的复活节岛树木稀疏、土地贫瘠、水土流失严重,
波利尼西亚人在来到该岛的时候,也带来香蕉、芋头、甘薯、甘蔗、
•环境的破坏和文明的毁灭
当波利尼西亚人定居此岛数百年后,人口数量迅速增加,
|
|
图片4、 世界名胜,复活节岛巨型石像:摩艾(Moai)
根据沉积层中的花粉分析显示,大约在公元800年左右,
环境的剧变也给岛民的生活习惯带来巨大的冲击,
|
|
图片5、 到处是未完成的辉煌
后略 |
朱学渊问:是谁惩罚了这些光棍?中国是“空巢”吗?
学者:中国正爆发一场“光棍危机”
新华社(5月6日)报道说,“
去年,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为116比100,
易富贤:中国将现光棍危机,四千万男人找不到老婆
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、中国人口学专家、《大国空巢》
新华社的报道说,“‘两非’
他说:“
重男轻女传宗接代观导致性别失衡
路透社报道说,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,
《大国空巢》作者易富贤表示,2005年-2013年中国有“
今年1月,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通知,
瑞洁:彻底废除坏政策才能解决性别失衡问题
美国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(Women’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)的创办人兼主席瑞洁(Reggie Littlejohn)表示,中国政府现在采取行动打击“双非”
《大国空巢》的作者易富贤认为,
据易富贤推算,1990年-2012年,
|
|
图片,北京街头休息的光棍
|
朱学渊: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(二○一四年增订微软电子版)
|
中国历史并不讳言开创华夏的夏、周、秦是戎狄部落,
•《尚书》和《逸周书》的由来
司马迁也曾经暗示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,
《百家》言黄帝,其文不雅驯,荐绅先生难言之。
尽管《百家》早已失传,但是古代大学者也读不懂的书,
|
|
图三十四 汉字蒙语《蒙古秘史》之一页
春秋时代流传着三、四千篇上古文字,孔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了《
•“虎贲”是蒙古语的“力士/壮士”
《尚书》中出现过四处“虎贲”,被〈周本纪〉引用的是〈牧誓〉
蒙古语“虎斯”是“强壮/有力”的意思。
〈汤诰〉“贲若草木”即是“人丁若草木[一般兴旺]”;
〈盘庚〉“用宏兹贲”中的“兹贲”即是“兹人/此人”。
“奋”也是“浑”的替字,〈舜典〉的“有能奋庸熙帝之载”,〈
能奋庸美尧之事者”,其中“能奋”就是“能人”。
“昆”也是“浑”的谐音,蒙古语除了是“人”,也是“兄长”
这些道理不仅孔安国和马融不懂,连司马迁和孔子也是不懂的,
•“荷罕旗”是“荷白旗”
武王灭殷后,在商都朝歌游行庆功时,〈周本纪〉记有“
略知北方民族语言的人都知道,蒙古语“白色”是“察罕/叱干”,
•“惟家之索”为何是“家道破败”?
〈周本纪〉引有《尚书•牧誓》之名句:
牝鸡无晨;牝鸡之晨,惟家之索。
意思是“母鸡不司晨;母鸡若司晨,家道就破败。”孔安国解释说:
但是,动词“索”是“索取/勒索”,并没有“至尽”的意思;
•“大禹”是“单于”
《尚书》有很多处“后/侯”,还出现过十处“诸侯”和八处“
惟仲康肇位四海,胤侯命掌六师。羲和废厥职,酒荒于厥邑,
此中“胤侯/胤后”应为同一人,即胤族的首领;“羲和”
其实,“大父/大夫/大禹/亶父/唐尧”的读音就是“单于/
上述讨论的“父/夫”与“后/侯”同音比较显然,而“尧/禹/
•结束语
三、四千年前,黄河流域发生了语言的转型,
|
|
图三十五 汉学大师伯希和
二○一○年六月一日初稿
二○一○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改 二○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再修改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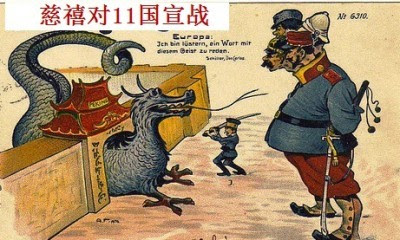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沒有留言:
發佈留言